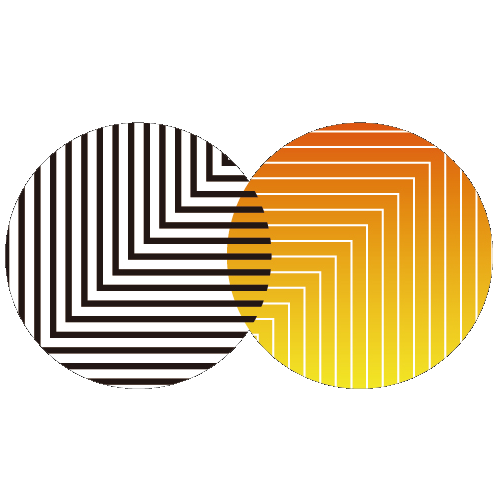約莫十多年前某天,起床後發現右眼前一抹黑影,經歷一連串就醫治療,是不可逆的黃斑部出血,開始調適接受失明的可能,過程中從絕望到接受,人生計畫的翻轉,從過往的同理心看待身心障礙,轉變為認知這樣的障礙,與日常的不便,是無法感同身受,而且無法言傳,不同的障別,不同的輕重程度,都有各自不同的狀態,無論如何認真傾聽,無論如何同理,他人完全無法體會。我們缺乏對障礙者的認知,以致於不知如何與障礙者相處。事實上就如同我們對一個人的優點羨慕或是嫉妒,但那優點同樣如人飲水,障礙者的障礙如同一般人的優點,不論是障礙還是優點都屬於一個人的特點,這些特點每個人都有,如何平等對待相互尊重,來取代同情與歧視,都能讓我們更往身體的平權邁進。
透過首次舉辦的「無限影展」,讓我有些驚奇,就如同紀錄片《極樂世界-自立人生》的開宗明義,並非消極的讓我們認知身障者做不到的事,而是企圖發現只有身障者做得到的事。這樣的積極性,一反我們主觀認定身障者的悲情與無助,幾部影片像是《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?》,全身肌肉萎縮,只剩下頭和手稍微能動,看來悲慘人生的鹿野靖明,卻任性毒舌,使喚著志工們貼身服侍,但他遠大夢想受到媒體關注,鼓舞了其他身障者,他的酸言酸語卻總有辦法讓人對他不離不棄,他的魅力如同原一男於1994年拍攝紀錄片《全身小說家》中的井上光晴。
以《淪落人》拿下今年香港金像獎影帝的黃秋生,片中因工傷造成半身不遂,妻離子散,孤僻又防人的性格讓來幫忙翻身起居的外傭都做不久,和 《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?》中的鹿野都以輪椅代步達成自主,但都需要他人協助方能生存,同樣都刀子嘴豆腐心,黃秋生將自我實現轉嫁到菲傭身上,不計代價助她圓夢,鹿野則透過壯大自己,來鼓勵身障者不吝逐夢。
因為靠眼睛吃飯,很難想像看不見後的人生,此次影展邀來了兩部與視障相關的厲害電影,一部是坎城金攝影獎、評審團大獎得主河瀨直美導演的《光》,永瀨正敏飾演視力逐漸消失的攝影師,原本如此專精於捕捉光線,如今將要全部失去,但透過口述電影,讓他聽到世界,建立情感連結,失去視力並不等同於失去生命,當他將和生命一樣重要的相機拋棄,他已準備好以心靈視窗來接受人生風景。
婁燁的《推拿》描寫的是「盲人推拿師」因為視障而放大了其他感官,靠自己的雙手工作,觸覺的肌膚接觸,在闇黑中更為敏感私密,因為看不見情愫反而更加濃烈,與人的連結更勝常人一籌。
身體的殘缺並非生命終點,當上帝關了一扇門,必打開一扇窗,生命自會找到出路,這適用於所有的人。